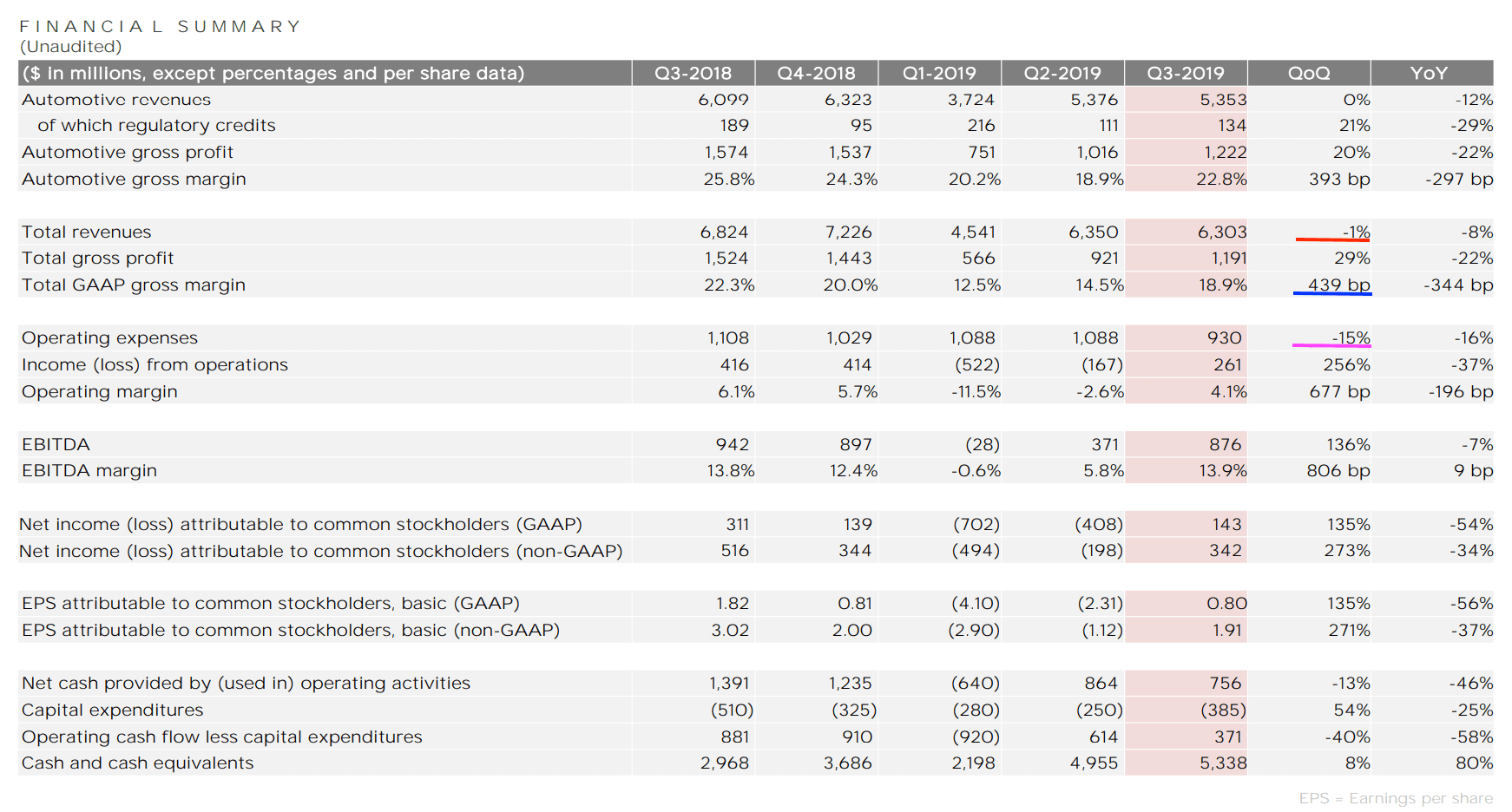閱讀時間 13 分鐘
最近許多國家領袖呼籲要伸張「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工商時報):
德國總理梅克爾呼籲 . . . 歐盟必須發展自家的資料管理平台,並減少對亞馬遜、微軟與谷歌等美國提供雲端服務科技大廠的依賴。
. . . . 包括福斯等企業以及德國內政部與社福系統等官方機構愈來愈多的資料都儲存在微軟與亞馬遜的伺服器,「此一情況等於逐漸喪失我們的主權。」
梅克爾是跟著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主張。馬克宏在八月呼籲拿回歐洲的數位主權(法國外交部):
歐洲過去很擅長擬定競爭策略 . . . 我們忽略了我們的產業策略。使得我們的工業與技術在許多領域都依賴他人。
. . . . 如果未來我們還想要製造電廠、環境保護服務、飛機以及國防科技,我們必定需要建立我們的主權。. . . 我們也必須追求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主權」是管理的權力。歐洲領袖擔心資料流入網路平台,管理的權力就流至美國。
不過,美國也沒有掌握數位主權。美國政府頭痛資料由網路企業把持,政府無法取得。我曾寫過的 FBI vs. 蘋果一案,便是 FBI 試圖逼迫蘋果在手機軟體中寫一個「後門」,讓政府可以破解。最後政府敗訴。
但美國並不死心。最近更協同國際警察組織向網路平台施壓(路透社):
. . . . 國際警察組織(Interpol)將於週一譴責強加密的普及,保護了兒童性侵犯。
該組織支持上個月由美國、英國與澳洲的執法單位的聯名信。他們將用難以逮捕兒童性侵犯為由,要求企業為持有法院拘捕令的執法單位打開用戶之間的通訊。
連署信草稿寫道:「服務商、app 開發者與裝置製造商正在開發、佈建帶有加密的產品與服務,等於掩蓋了平台上兒童被性侵的事實。」
「科技公司應該在其產品的加密設計中加入機制,讓擁有合法授權的政府能取得可讀且可用的資料。」
但網路企業說,真正掌握權力的也不是他們。控制企業的是顧客 — 是顧客要求這些工具的。臉書的發言人回應(路透社):
「這提案會危害需要強加密來保持安全的人,包括免於被駭客或是迫害政權的侵害 . . . 這亦會削弱超過 10 億人的線上安全。」
看出來了嗎?歐洲要從美國身上拿回數位主權。美國要從企業拿回數位主權。但企業說真正有權力的是人民。
再把上述的關係鏈縮短,會發現權力的「淨流動」是國家權力減少,個人權力擴大。造成這個結果的是科技。
個人權力的擴張
科技放大個人的力量,這已是老生常談了。但大部分人還是會低估改變的速度。
我們用 30 年來對比。在 1989 年,一個年輕人只能從電視或報紙上讀到天安門事件。他的朋友圈就是同學與同事。他的職涯選項不是做公務員、捧鐵飯碗;出國進修,希望投入教職或是進入公司做管理層;或是創業。
創業並不容易。除了認識的人才有限之外,他還必須取得土地與設備,從幾家銀行爭取貸款。他的人生楷模可能是王永慶 — 靠著買賣米跟布起家,最後透過政府的援助而建起了塑膠廠。也可能是蔡萬霖(國泰集團),掌握許多土地。無論如何,他必須取得實體資產,並且跟政府打好關係。
到了 2019 年,同樣年紀的年輕人有廣闊的資訊來源。他可以在網路上結交不同領域的人才,向大眾或私人基金募資。創業的最大困難大概不是取得實體資產,如土地,而是要創造品牌、開發特殊知識、吸引無限的用戶注意他。他的楷模大概是馬克佐伯格或是馬雲,都不到 50 歲就靠著軟體而成為巨富。他認為自己應該有能力,也有資源實現更大的夢想。
1989 年的人可能覺得更平等 — 大家都比較窮,機會一樣少。但 2019 年的人能直覺感受到自己的潛力,也更清楚意識到妨礙他實現潛力的阻力,包括官僚、習慣、競爭等。最大的差別是網路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cyberspace)。2019 年的人在虛擬世界中跳脫了實體的桎梏,感受到更自由、更有效率。
而虛擬世界也不只是逃離之處,很快地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我們從工業時代進入資訊時代,主要的經濟價值也從實體資產轉到無形的知識。今天最重要的公司都是知識型公司,靠知識而非資產賺錢。財富向擁有知識的人聚集。掌握虛擬世界的人可以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甚至獲取實體世界的權力。
然而這也代表掌管實質資產的國家,權力被嚴重削弱。
現代國家的價值
政府的原點是保護兩種實體資產:人與土地。在農業時代,耕作需要多人、長時間的合作;用武力奪取的效益顯然很高。因此為了保護收成,就出現了基本的政府 — 人民付稅給武裝團體,由武力團體保護人民與財產。
現代國家(nation state)大致延續此一結構。只是工業革命與彈藥出現之後,武器更加強大,導致現代國家需要更徹底地集中資源,才有足夠的防禦能力。政府更大,也深入更多面向,包括維持正義(法院)、分配利益、劃分財產、實施計劃經濟等。但政府調動的仍然是實體資源。
而且國家是有機體,會成長,也會想要維持自己的存在。於是政府就像壟斷的企業一樣,不自覺地膨脹,涉入越來越多業務。
如果政府能創造更多價值,那也還好;但卻沒有辦法。
國家效益的降低
越多價值來自虛擬世界,國家提供的價值看起來就越差。
舉例來說,過去台灣政府建中山高速公路,顯著地提高了全國的生產力。我們覺得政府做得好 — 效益很高。
但現在沒有高速公路需要建了。再建一條高速公路的效益有限,因為更多價值在於虛擬世界的交易。
或者問:政府要如何創造下一個台積電?這次不能靠提供土地或是資金了。土地與廠房是台積電價值最低的資產(與國泰集團不同),而外部資金非常豐沛。台積電真正的價值是知識、人才、流程、文化,全部都是無形的。如果中共真的有朝一日佔領台積電,也無法取得台積電的價值 — 廠房不會運轉、技術不會進步、客戶沒有信任。中共還不如買下台積電。
因此政府現在在推動創新上能做的,不外乎給予稅賦優惠、環評快速通關、上市法規鬆綁等 — 全部都是政府在降低自己的干預。
同時,隨著實體經濟的價值降低,人們也不需要生那麼多小孩了 — 多三雙手不如培養一個聰明的腦袋。所有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都大幅降低,人民受教育時間大幅延長,存活率也大幅提高。這代表政府未來的稅收更少,要付的養老津貼更多。還能用來創造價值的資金就更少了。
三重打擊
因此現代國家實際上面對三重打擊:
- 自身膨脹導致營運成本提高
- 稅收基礎縮減使得資金降低
- 實際提供的新價值減少(因為價值在知識)
合在一起,就是國家看起來效率越來越低落。
最明顯的後果是不論世界各地,所有人普遍地鄙視政客與政治。大家或許很難想像,30 年前的許多人認為投身政治是高貴、貢獻社會的事。現在卻被視為只是想分贓利益 — 便是因為看不見政府的價值。
而人民對政府的反應分兩種。「菁英」,也就是擅長虛擬世界的人,對政府的綁手綁腳越來越不耐,開始往限制更少的國家,去工作或移民。「一般人」則看著貧富差距擴大、競爭越來越激烈,對於幫不上忙的政府越來越憤怒。於是他們投向同樣憤怒,並且承諾能撼動現有體制的候選人。
而國家為了持續營運,鞏固正當性,有幾種常見的做法:
- 找替罪羔羊:把問題歸咎於他者。例如移民、大型企業、有錢人、更大的官僚組織(英國說是歐盟,台灣說是中國,中國說是美國,美國說是聯合國)等。
- 加稅 / 印鈔票:將人民的錢移到政府手中。
- 限制流出:不讓富人移民,不讓企業將錢移出海外,以及不讓資料流到虛擬世界 —「數位主權」。
最終極的作法,是把一切都變成國家的。
極權國家機器
為何近年來極權國家對人民的控制越來越深入,到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管的地步?如中國的網路長城、信用分數、臉部辨識、國家數位貨幣,現在甚至還推出「愛國 app」,要求人民按時做功課?為何極權國家更頻繁地用關閉網路來控制人民,例如伊朗與傳言中的香港?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個人能力擴大,政府就必須縮小個人的活動空間,否則動亂隨之而來。
在農業時代,國王只要在城鎮的四個城門放上衛兵,就能維持權力。人民的財產在城內、家人在城內,逃不出手掌心。因此國王不太需要知道城內的人民平常在聊什麼、想什麼、買什麼。
然而現在城內的人民可以去虛擬世界 — 把錢跟資源存在虛擬世界,在虛擬世界組織、集結。反對的力量可能突然湧現。因此國家為了鞏固權力,必須跟著監控所有進出虛擬世界的行為。
未來國家與個人主權
工業革命與槍砲推翻了帝國,網路與駭客會不會推翻現代國家?
我想至少會經歷一段動盪的重建過程。如 1215 年的英國《大憲章》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最終人民與政府會需要簽一個新的合約,重新規範雙方的權利義務。而這一次人民將要求再次擴張權利。
哪些權力?有些科技圈人士提出「個人主權」(sovereign individual),認為個人(相對於政府)應該控制更多資源,來維繫個人的自由。例如,今日你看似自由,實際上土地的記載是國家說了算,存款是銀行說了算,水電瓦斯與網路由國家控制,資料則在網路平台手中。
「個人主權」論者主張,未來應該「還權於民」。貨幣不受國家控制(如比特幣),財產登記不需要國家(如區塊鏈),水電網路去中心化,資料存放在個人的伺服器中等。這裡不詳談技術與經濟上的可行性;重點是科技再一次擴大人民的自由,限縮政府的權力。
當然現代國家不會願意、極權國家不會願意,甚至現在的網路企業也不會願意交出控制。今天還有許多人缺乏基本的權利與自由,更遑論是進一步的權利。轉變不會容易。
但即便在有「個人主權」的時代,實體世界仍然重要,因此國家 / 政府也仍然重要。政府的角色會轉為專注於解決科技無法處理,甚至造成惡化的問題上,如貧富差距、壟斷、環境污染、健康、人權等。馬克宏嘗試描繪法國在未來世界的價值:
. . . . 貧富差距破壞了我們經濟系統的正當性。當我們的同胞沒有分到好處,我們如何跟他們說這是正確的系統?這影響到我們的民主的平衡。自 19 世紀以來,民主體系、中產階級的擴大以及市場經濟形成了進步的三個支點。當中產階級無法再分享好處,他們就會懷疑,並合理地受到極權或非自由民主國家的吸引 . . . .
. . . . 法國的精神是受共同的感召而起身抵抗。擁有抵抗精神代表不向命運投降,也不放棄適應。 . . . 我相信歐洲的特質,以及貫穿歐洲的使命,是真正的人道主義(humanism)。. . . . 美國也同在西方陣營,但其提倡的是不同的人道主義。他們不太在意氣候、平等或是社會的平衡。他們重視自由甚於一切。. . . 委婉地說,中國集體的優先事項也與我們的不同。我們是唯一一個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任何需要重新站起的時候,把人類放在中心的區域。看到當前的混亂,我相信這將再一次成為我們的目標。
馬克宏常被批評愛說空話。但我引用這一段是要說明,國家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因為定位已經不再明顯。而這個定位會圍繞在人,在實體世界。
國家會繼續努力從虛擬世界中抓回權力,或是控制人民、宣揚其存在意義。但最終能向前跳躍,證明自己價值的國家,會專注於真正需要調動實體資產、靠人與人面對面溝通的工作。這些國家會與虛擬世界合作,讓個人穿梭其中,而國家分享在虛擬世界所激盪出的想法與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