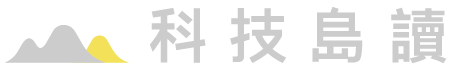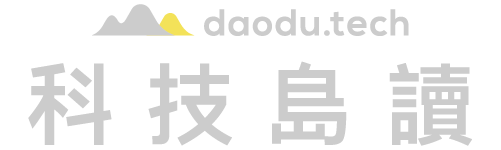閱讀時間 10 分鐘
必要人士
此次疫情中,在所有禁止移動的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或倫敦,都有一批人例外。他們可以照常工作,甚至必須照常工作。他們是從事「必要業務」(essential business)的人。例如舊金山定義以下為必要業務:
- 醫療院所
- 超市、雜貨店、菜市場
- 農田、畜牧、養殖與捕魚業等
- 報紙、電視、廣播
- 加油站
- 水電行
- 消毒、除蟲人員
- 郵差與遞送服務
- 洗衣店
- 餐廳(限外賣)
- 學校(須遵守社交距離)
- 飛機、計程車、叫車平台、電動滑板與單車分享平台等(僅供上述必要業務使用)
- 居家照護者
而剩下的人所從事的,自然就是「非必要」工作(non-essential business)。大部分人(包括我)赫然發現,原來自己的工作是非必要的!
同時你可能也注意到,上述工作都是一般人覺得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將來從事的工作。醫師跟機長是少數例外。為什麼我們大部分人都從事「非必要」的工作,「必要」的工作卻報酬很低?
槓桿決定報酬
因為市場認定這些工作的價格很低。我在「富裕與付不起」中把工作分類為兩種:提供商品與提供服務。提供服務者就是上述的「必要」工作者。他們真正提供讓人更健康、安全、舒適的服務。但他們的工作沒有「槓桿」(leverage),每一段時間只能服務一些人。因此他們的報酬也有限。
另一批人是提供商品者。而商品就有槓桿 — 商品可以不斷複製,服務更多的人。因此他們獲得更大的回報。還有許多人的工作更抽象,他們服務的是市場本身。他們的存在是為了讓市場更有效率,例如律師、金融人員,甚至是一般管理人員。這些人也有槓桿;他們可以從市場效率的提升獲得更高報酬。
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 David Graeber 稱那些沒有直接為人們提供價值的工作為「假工作」(bullshit job)。他指出一個弔詭的狀況:經濟學家凱因斯在 1930 年就預測隨著生產力持續提升,20 世紀末的美國與英國人,將可以一週只工作 15 小時。但為何我們今天還是整天加班?
答案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偏差。Graeber 指出市場經濟的確促進科技發展、生產力上升,讓數十億人脫貧。今天全球的生產力足以讓所有人都有基本的健康與享受。然而「市場至上」主義導致人們只追求市場能反映的東西:價格。例如企業不斷追求利潤,將提供「必要」工作的人貶抑為只是可替換的零件成本。企業鼓勵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不斷刺激人們買新的東西。於是人們必須加班賺錢,或是為了賺錢而做無法帶來滿足感的「假工作」。
此次疫情凸顯了市場的另一種偏差,就是為了追求效率而犧牲韌性(resiliency)。韌性是指面對衝擊的準備。例如許多人批評現在急待政府紓困的企業,如航空公司、電影院業者,為何不在賺錢時多存點錢,未雨綢繆?口罩公司為何不多存一點口罩?銀行多留一點存款(不要放貸)?
但是市場不允許。競爭導致企業必須追求投資報酬率,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營收。就算賺錢了,首要之務也不是存錢,而是發股息、買回自家股票(share buyback),或是再投資。這些作法會降低股本,提高每股利潤。此外,企業盛行舉債募資,因為債也不會稀釋股權。就算企業原本想存錢,也會被競爭者逼的擴大支出。
股息流回股東身上,也就是一般家庭,仍然會被捲入市場的漩渦中。家庭也不斷努力提高「效率」,追求更好的消費。家庭也不存錢,而是投資在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學區,購買更多享受,甚至背負許多房貸。就算某個家庭想存錢,其他人的消費也會墊高所有人的成本。
落在個人層面,則是加班,不斷尋找更高的薪水,然後買上述的產品與服務。一切是為了在更短的時間,得到更多享受。
市場用價格驅動供需,但價格很難反映提供服務的人的社會價值,也不鼓勵囤積韌性。企業沒有現金,卻有貸款,遇到疫情衝擊就得裁員。家庭沒有儲蓄,只有房貸,失去收入時就瀕臨破產。個人沒有累積健康、個人滿足感,以及與他人的情感連結,在失去工作時就頓失生活重心。
這場疫情突然停止市場的運轉。經濟中缺乏韌性的部位一一現身,逐漸停擺。同時,人們發現沒有市場的指揮,不知自己為何而戰。許多人只想趕快恢復「正常」狀態。
休眠與復甦
人類大病之後要恢復,當然很艱難。通常病好之後,人生觀也會變得不太一樣。經濟也是如此。
有些人認為現在是「戰時狀態」,需要「戰時動員」。這不太對。戰爭時的經濟措施是政府開出大量需求,全力提高生產力,促進大量經濟活動,才能製造大量的物資與武器。以人體比喻,這像是打一針腎上腺素,讓人出拳能虎虎生風。
但對付疫情則相反。此時需要的是降低經濟活動、減少社會動員,也不要增加生產 — 生產了也沒人買。這比較像是把病人放入冷凍修眠狀態。
當然也不能休眠到停止呼吸 — 還是必須維繫基本系統運轉。血液還是必須在流。因此政府發動了兩波紓困措施(第一波 600 億、第二波 1,500 億以及 7,000 億貸款),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
- 抗疫:整備醫院、徵用醫療物資、補償居家檢疫、購買檢驗試劑等
- 延後成本:低利貸款、緩繳貸款、延後收稅、緩繳電信費等
- 替代需求:內需型企業的補貼、薪資補貼、技術研發補助、弱勢家庭生活補助等
簡言之,除了抗疫之外,政府希望減低企業與家庭的成本,或是至少延後支付成本的時間。同時政府也代付一部分企業損失的收入,以及個人損失的薪水。
在理想狀態下,以上是短期措施。希望幾個月之後一切能恢復正常。但長期來看,顯示了當市場失靈時,需要政府挺身而出,救濟市場的不足。因為政府與市場是根據不同的邏輯運作。
政府與市場的邏輯
市場平常運作順暢。「看不見的手」讓供過於求的東西減少生產,供不應求的東西增加生產。越有效率、能要到更高價格的企業或個人是市場的贏家。
然而如上述,在市場無法反映的部分,例如人性的尊嚴,或是整個系統的韌性,就需要政府來救濟不足。因為政府不是市場邏輯,追求的不是效率,工具也不是價格。政府的職責是提供人民的福祉與健康。因此當口罩、酒精缺貨時,由政府接手市場,直接生產,不計價格。接下來政府還要組檢驗試劑國家隊。未來隨著紓困措施實施,政府會參與到更多經濟層面。
這一次各國抗疫的成效,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政府接手市場的速度。如美國、英國等高度尊崇市場經濟,排斥政府干預的國家,政府接手的速度就慢的多。美國政府主要還是透過市場推動防疫,由政府給企業錢,或是呼籲企業挺身而出。但這跟亞洲「家長型」政府相比,就顯得緩不濟急。(雖然美國市場的能量一旦發動,會非常可觀)
事實上政府原本就提供水、電、瓦斯、基礎教育,以及在台灣的健保。此次疫情只是再次說明政府干預的價值。未來政府也會提供寬頻網路、電腦,甚至是就業與「國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國民基本收入的邏輯是:政府發錢給人民,是因為政府的職責是讓人民健康地生活。不是因為人民創造了某種「價值」,具有某種「價格」。這跟美國獨尊市場,「不工作就等著餓死」的價值觀非常不同。
未來政府與市場會持續分工,同時合作。兩者的分工呈光譜分佈。一邊的極端是美國:盡量由市場決定一切,政府服務市場的主角(企業)。另一邊的極端是中國:政府操控一切,市場填補政府不在乎的領域。
關鍵在於兩者如何搭配,適時地調整位置。而科技會決定調適的速度與精準度。
更有韌性的未來
今日世界遠比 1918 年更能調適。麻省理工學院與兩位聯準會董事最近共同提出研究報告,指出在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期間,美國尚沒有聯邦層級的防疫組織。各地城市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辦法面對。有些城市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有些城市則為了保護經濟,只有寬鬆的管制。研究指出,嚴格干預的地區不但致死率較低,疫情後的經濟恢復得也更快。
今天疫情散播得比 1918 年更快,但我們應對的手段也更多。至少台灣證明了政府可以快速有效的接手市場,調度資源。科技將會更強化社會的反應。
例如,科技可以追蹤人類的移動,也可以監視人的身體狀況。物資的流動可能會登錄區塊鏈,不會有「口罩跑去哪」的疑惑。金融系統可以讓紓困的資金更快、更精細地分佈,例如直接匯到人民的帳戶,或是限定只能用於特定花費類別。學生上課的進度、家庭觀賞娛樂節目的時間也都更容易管理。醫院、民間組織等也更容易發起、協作、回應政府以及求援。
當然以上有隱私與政府擴權的疑慮 — 科技永遠都是雙面刃。如何遏止政府過份干預市場,以及保有人民的自由,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但至少從防範、抗疫與復甦經濟的角度,20 年後的行政院長碰到類似的疫情,會比今天的行政院長更輕鬆。
康復之後,我們也不該忘記疫情凸顯的問題:市場的偏差貶低了人的價值;讓企業趨於脆弱,讓個人趨於貧脊。復原的人不該急著回到讓他生病的生活方式,而是想想真正必要的是什麼。